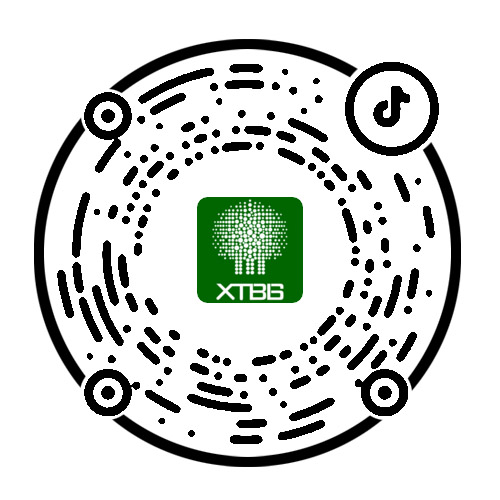中国科学报:守望珍稀植物最后的“家园”

多脉汉克苣苔(发现于云南河口,蔡磊供图)

粗筒螺序草(发现于广东英德,吴磊供图)

左:杨氏马兜铃(发现于云南保山,朱鑫鑫供图)
右:大籽假龙胆(发现于新疆伊犁,亚吉东供图)

金沙江吊灯花(发现于云南丽江,吴之坤供图)
最新出版的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PhytoKeys以“发现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为题,针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及其对中国植物多样性和特有性中的作用出版专刊,聚焦中国植物多样性的新发现。该专辑刊登了18篇文章,描述了23个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德铢在专刊综述中表示,“通过与国内研究院所和高校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调查和保护等方面的广泛合作,我们组织了一期以‘发现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为主题的专刊,旨在介绍中国植物学家近期的最新发现,促进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植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研究。”
物种最后的栖息地
1988年,英国生态学家Norman Myers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下简称热点地区)的概念。热点地区的划定除了考虑该区域的地质历史和生物区系的自然性以外,还需要达到两个指标:至少有1500种特有植物;超过70%的原生植被已经丧失。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蔡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提示,实际上,有很多热点地区远远超过了其设定的指标,例如中国西南山地至少有4000种特有植物;东南亚的巽他古陆(Sundaland),即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地区的特有植物高达15000种;在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森林(Atlantic Forest)地区,原生植被仅剩8%。
人类正在经历地球历史上继恐龙灭绝事件为代表的第五次大灭绝之后,由人类自身介导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在有限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情况下,无法对全球所有的区域和物种进行全面保护。而热点地区的划定,有利于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要素。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研究组博士郁文彬作为专刊共同编辑,邀请了综合保护中心和园林园艺部蕨类研究组等科研人员,在专刊中贡献7篇研究论文,涉及9个新种。“热点地区是特有种和稀有种最后的栖息地,如果丢失的话,这个物种就会面临灭绝。”郁文彬说。
“因此,热点地区由于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消失殆尽的原生环境,可能已经成为某些物种最后的‘家园’,是必须优先调查、研究和保护的重点区域。”李德铢强调。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达到36个。中国国土范围内有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即中亚山地的东部,包括了新疆的天山,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山区;喜马拉雅地区,在中国境内的部分位于青藏高原南缘的高原地区;中国西南山地,其绝大部分区域位于我国境内的西藏、四川和云南,印—缅地区,其东北部从云南西部开始至广西,并沿中越边境滨海地区延伸至广东东部,包括整个海南岛。
据初步估计,分布于中国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维管植物种类应该不少于25000种,约占中国总数的3/4。
“近六年来在中国发现的植物新种超过1000种,73%的物种来自热点地区。对热点地区的植物调查和研究,是认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可以进一步促进对中国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国的植物种类占全球植物总数的1/10,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李德铢说。
对中国生物多样性更全面的认识
本次专刊共报道了23个植物新种,其中20种都来自上述4个热点地区。这些研究结果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植物多样性的资料,也为其中某些植物类群后续开展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相关基础信息。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专刊中报道了夹竹桃科吊灯花属一个新种。贵州中医药大学博士吴之坤介绍,2015年8月,在滇西北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时,他们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吊灯花属植物。“这种植物从形态上来看,与所有中国产的吊灯花属植物都有很大差别。”
吊灯花属植物主要分布于非洲和印度次大陆,其中的一些种类为著名的多肉花卉,而这个新物种仅分布于云南—四川交界的金沙江河谷地带。“‘金沙江吊灯花’的发现,再次表明中国的某些热带植物种类与其非洲的‘亲戚’关系密切。”吴之坤认为,这在生物地理学上对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河谷地带的植物来源有重要意义。
当时国际吊灯花属专家审稿时,对在中国发现这样一个形态特别的新种感到非常兴奋,对于中国产的吊灯花和非洲、印度的种类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希望开展深入合作研究。
热点地区是需要优先开展调查和保护的重点地区,但热点地区之外的“非热点地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专刊中有3个新种是在热点地区之外发现的。例如,我国的川东—鄂西地区并非热点地区,但仍然拥有众多的特有植物,也是水杉、银杉、银杏等“活化石”植物的自然分布中心。“我们对2013—2018年期间报道的国产植物新种进行了分析,发现大概有27%的植物新种分布在热点地区之外,在‘非热点地区’的调查结果仍然可以促进我们对中国生物多样性更全面的认识。”李德铢说。
据郁文彬介绍,虽然此次专刊中报道的植物新种在野外调查时采用的是传统调查方法,但新软件和新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效率。“比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自行研发的biotracks手机App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快速记录野外采集信息。”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运用,也为植物新种的发现,提供了除形态比较之外在核苷酸序列差别上的证据。“将分子技术融入到植物分类学中,这让植物新种的发现更加具有说服力。”郁文彬表示。
为热点地区调查培养后续人才
多年的热点地区调查工作让李德铢团队意识到,需要帮助保护区提升自身的能力建设,“建立其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兴趣并实现‘造血功能’”。
近年来,李德铢团队规划了一些联合开展的项目,带动地方保护区组建自己的专业团队。“国家近年来非常重视对保护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能力建设,一些工作在保护区一线的技术人员也逐渐成为地方专家。现在很多保护区不但欢迎专家前来开展调查,而且一线技术人员也不再只做带路人、负责一些后勤支持,而是更进一步参与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研究的第一线。”
专刊中有两个物种,最早的发现者就是当地工作在保护区和林草部门一线的技术人员。
虽然人工智能、各种植物识别软件近几年来大量出现,大有代替专业分类学家的势头,但由于植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尚未能通过机器学习而得到可靠而满意的分类。
“经典分类人才的萎缩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李德铢提示,虽然现在国家相关基金会对经典分类项目有所倾斜,但在项目经费、个人发展等方面受到“主流科研”(以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为主要产出目标)冲击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此外,经典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希望在政策上不要设定严格的“按时交卷”、“让从事经典分类的年轻学者可以更好地沉淀,专心致研。”李德铢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