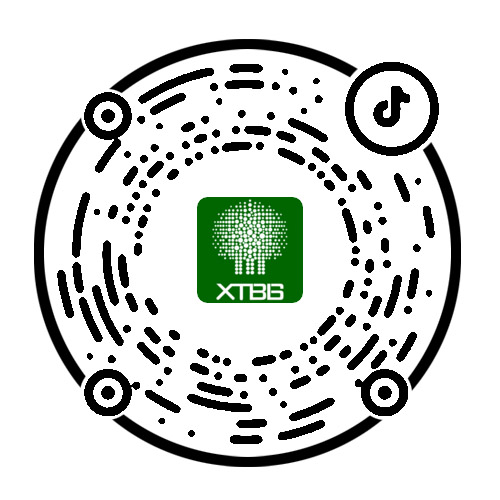中国科学报:保护研究 不止需要科学家

余翔林摄
■本报记者 胡珉琦
“我们将沿着众人向往的滇藏线和新藏线,途经森林、灌丛、荒漠等植被类型,用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一起探索高原植物的奥秘。”
这个夏天,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森林灌丛生态系统调查子项目面向公众招募志愿者,只要是有植物分类学基础的爱好者、自然爱好者、静物摄影爱好者,都可以申请报名此次对西藏中西部的植被调查。
这是第四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公众科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中的一个案例。事实上,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众科学项目已经在发达国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科学与社会效益,公众科学家开始成为科学研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势力。
公众贡献数据,科学家贡献知识
森林灌丛生态系统调查子项目的组织方——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是通过一个名为“Biotracks”的公众科学平台发起这次招募的。
Biotracks于2016年诞生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它是一款可用于自然观测记录、具有科学考察功能应用的App,采用公众科学与开放科学的模式:无需笔记本、地图、GPS记录仪,任何使用者都可以随时记录物种照片和自然景观,并生成专属的个人自然观察地图;记录GPS轨迹,在任意位置生成拍摄点;搜索物种照片,感知周边轨迹和图片信息……
Biotracks最新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支持发起科学项目,包括公共项目、团队项目和私密项目。比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植被生态学与植被图志编研研究组发起的2019南迦巴瓦春季植被调查、由中国科学院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美丽中国”项目支持的甘肃和宁夏国家自然保护区植物调查等,除此之外,有大量项目聚焦于高校分类学教学和野外实习。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Biotracks用户公开照片集已经超过100万张,覆盖了1.7万个生物物种,60万个地理位置,目前运行的科学项目超过800个。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真正由公众、科学志愿者、科学家群体一同参与支持的共享平台,目标是完成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地图的绘制。”昆明植物所标本馆数据研发中心主管、Biotracks的设计者徐洲锋花费了3年时间,才让这个平台正式上线。
实际上,Biotracks的模式并非原创。200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就制作了一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都颇受欢迎的自然观察社交平台iNaturalist。
除了记录、分享所观察的物种,公众可以从iNaturalist 社区接收到科学家对物种辨认的建议,讨论、帮助其他用户辨认他们所观察的物种,还可以追踪由其他用户及公众科学家组成的、有关特定区域及物种的任务群组。搜集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检测生物多样性变化。2017年,iNaturalist还成为了美国加州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联合项目。
徐洲锋认为,iNaturalist最典型的特质就是公众贡献数据、科学家贡献知识、平台作为连接桥梁,并且它完全是由爱好者自下而上发起的。“这种公众科学项目的实现路径在国内很难照搬。”
公众科学如何让科学不缺位
在全球范围内,最著名的公众科学实践者要数1915年美国奥杜邦协会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创办的康奈尔鸟类实验室。基于这个实验室管理的几个公众科学项目,搜集了大量数据服务于生态学研究,并且直接推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
康奈尔鸟类实验室运行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公众科学在生态环境领域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职业科学家的认可和重视,这也反过来促使更多的公众科学项目得以“繁衍”。
在国内,虽然公众科学的意识在近几年得以萌发,但实践过程依旧困难重重。
台湾大学森林环境资源学系助理教授刘奇璋在美国读博期间就专注科学教育、正式及非正式教育、公民科学的研究领域。他谈到,根据公众科学的一般定义,它本质上必须由科学家主导,大众是科学研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参与者,包括最初探索问题、搜集与分析资料等等。“问题是,在许多所谓的公众科学项目中,科学的目标、科学家的角色是缺位的。”
对此,徐洲锋也深有体会,“中国的科学家普遍没有做好准备。现有体制不给予积极的反馈,他们也就难以产生热情。另一方面,一般公众的知识储备不足,也常常让科学家产生对项目预期的质疑”。
他坦言,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我们的科研传统主要是满足国家需求,由专业人员集中力量办大事,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意识去主动觉察这种由一般公众或者某个科学家个体关心发起的研究议题”。
在国内,公众科学项目往往交由一些社会组织发起和管理。而这种模式的风险在于,这些组织本身的科学专业程度良莠不齐。
因此,Biotracks设计之初,徐洲锋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真正建立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关联。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想办法吸引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加入这一平台中。
为此,Biotracks选择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成长策略,它最初的目标其实是为中国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开发出最好的数据采集工具。
这一平台最早是帮助科考队员疾速记录野外标本采集信息,自动编排采集号,记录经纬度、海拔高度、行政区划、采集时间等信息,并将野外照片、标本记录、数字标本、科考轨迹便捷地关联起来,以地图的形式将集合的数据反馈给科学家。
徐洲锋调查发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最核心的落点其实是在标本馆,但标本馆内部往往缺乏有效的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效率低下。由于Biotracks支持跨类群跨数据库的应用与整合,让其与Kingdonia标本管理系统对接,就可以为各地标本馆提供新型标本数字化方案支持。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数字化效率和质量,同时也形成了内部的规范化管理,还节约了大量成本。
通过向科研机构、专业人员展示Biotracks的系统优越性,的确对它自身的推广和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Biotracks优先聚集起一批专业用户,影响他们的理念、意识,然后在2019年才正式向公众开放,顺理成章地将专业研究者与公众科学家连在一起。
关注公众科学家的成长
利用公众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数据搜集,公众科学可以为调查、监测和保护生态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这是有证据、可评估的。不过,对于公众科学参与的学习过程和结果,以及公众科学参与中知识的构建和获取方式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大多数科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公众科学家搜集的数据,而不是公众科学家。”刘奇璋告诉《中国科学报》,实际上,建立、运营和维持公众科学项目是非常有难度的,对公众科学家本身的研究有可能帮助这一群体稳定、持续地成长,这也是公众科学本身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刘奇璋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兴趣点正在于此。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台湾地区最著名的公众科学项目“台湾动物路死观察网络”(TaiRON)。TaiRON是诞生于社交网络的一个虚拟社团,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专业人士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公众科学项目的核心成员。
TaiRON参与者会拍摄和上传野生动物车祸的照片和地理位置到互联网数据库,通过大量记录的搜集,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找出路杀热点、好发季节和受威胁的物种,提出及时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部分道路因此修建了防护网。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野生动物路死资料和标本目前还是台湾地区狂犬病疫情监控所需检体的最主要来源。因为在2013年,台湾发现了自1961年以来的首例狂犬病病例,竟然是一只路死鼬獾。
2015年,TaiRON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的“农地鸟类中毒事件调查”,是通过疑似农地鸟类中毒记录和检体采样的方式,找出作物与农药种类危害野生动物之间的关联性,将其作为制定特定农药使用规范的依据,降低环境毒害事件的发生。
目前,TaiRON 的会员已经从2011年成立时的10几人增长到约15000名。刘奇璋采用实践社群理论,对TaiRON项目的参与者进行了内容分析、观察和访谈,发现他们的内部运作是符合这一理论原则的。
比如:TaiRON 成员认同团体的核心价值观,有共同关注的议题;制定了一套共享的工作方法,成员参与联合的行动和讨论,相互帮助,分享信息;所有参与成员都对特定的领域拥有其深入的知识或热情,使他们能够为不同主题的工作作出贡献;等等。
未来,刘奇璋希望更精细地去了解公众科学家学习的过程、学习产出的不同面向,以及观察一个新成立的公众科学团体的完整发展过程。
“从公众科学家的研究视角,我的期许是我们需要突破‘同温层’,让现有的参与者尽可能去影响人际系统中的其他人,影响那些原本来自不同话语体系、不同认知体系的人参与公众科学。”刘奇璋说。